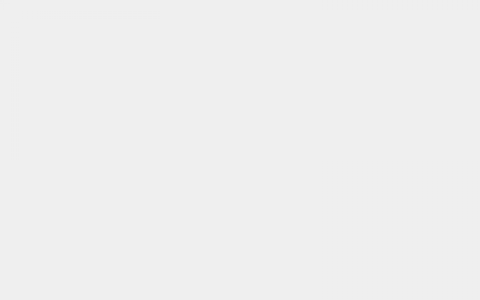风波亭里满江红是什么生肖?
风波亭里满江红是什么生肖
《满江红》上映至今,虽然票房成绩喜人,但也受到了一些争议,在竞争对手与饭圈黑粉的轮番拉踩之下,目前最匪夷所思的指控,就是“辱女”。而这顶大帽子的由来,即片中鹰犬逼问行刺者时,做出强......接下来具体说说
电影《满江红》的最大漏洞: 风波亭里的岳飞写不出三十功名尘与土
抗金英雄岳飞临死前在风波亭写下满江红,知道的人只有假秦桧。可是,词中明确表达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心志,丝毫没有风波亭的英雄末路之感。而且,岳飞这时已经39岁了,怎么还会写三十功名尘与土呢?身陷囹圄,还怎么“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一起来看满江红的五个常识。
一,词牌名。
满江红是一首婉约词牌,意境是很优美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诗: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满江红是一种水草、水花,在阳光下格外娇艳,引发文人的阵阵诗情,并不是后人以为的大开杀戒、血染江水的意思。
二,英文译法
如前所述,满江红是婉约意境,并非暴力文化,如果翻译为all river red,甚至all river blood,就离题万里了,还不如直接音译为ManJiangHong。
三,作者
满江红最著名的有三首,作者分别是柳永、岳飞、辛弃疾。
柳永《满江红·敲碎离愁》,显然是一首离别词,敲碎离愁,纱窗外,风摇翠竹。人去后,吹箫声断,倚楼人独。
辛弃疾《满江红·暮雨初收》,是一首思乡词,游宦区区成底事,平生况有云泉约。
只有岳飞那首《满江红·怒发冲冠》不是婉约词。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一首满江红,奏响了华夏民族抗击外侮的最强音。
作者是岳飞,这还有疑问吗?确实是有疑问的。虽然这首词无比贴切地反映了岳飞抗金失利的心境,但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证明是岳飞所作。众所周知,宋孝宗时已经为岳飞平反,谥号武穆,岳飞后人没有理由不在岳飞文集中收录此词。按照电影《满江红》的说法,秦桧命全军复诵满江红,天下尽知,可是满江红最早到元朝的元曲中才有雏形,明朝抗击后元才大行于世,如果这都能说得通,相信明教教主张无忌也会引用满江红对赵敏说: 还没吃到胡虏肉,不想结婚。
四,踏破贺兰山缺指的是哪儿?
贺兰山在宁夏,当时是西夏的管理范围,和宋朝和岳飞八竿子打不着,这就看作者是写实还是写虚了。写实,确实不沾边;写虚,可以解释为借用汉朝故事抒发抗金志向,后面还写了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其实,除了这两种解释,还有第三种解释: 贺兰山指的是河北邯郸的贺兰山,是岳飞抗金的必经之路,现在当地还有待召村,就是岳飞率领大军原地待命的地方。
五,满江红出现在中小学课本里吗?
精忠报国抗金名将岳飞屈死风波亭,一首《满江红》让人荡气回肠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滚滚历史长河中,曾涌现出大批杰出的影响中国历史的风云人物。他们或是杰出的外交家,或是卓越的科学家,或是引领国家走向昌盛的*治家。但是,对于我自己而言,我是最敬佩这位有着为国捐躯的豪情的军事家-岳飞。岳飞,字鹏举,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战略家、军事家和抗金英雄。
岳飞出生在相州汤阴县永和乡孝悌里的一个普通的农民之家。据说岳飞出生的时候,恰好有一只大鹄鸟从岳家屋顶飞过,并且发出高昂的鸣叫声,岳飞的父亲感到十分惊讶,于是他的父亲岳和就给他起了个单名叫做飞,又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鹏举。
黄河之水浩浩汤汤,奔流不息,伟大的黄河养育了中华民族,但是每当它怒气狂发,变得桀骜不驯时,就是中华民族的灾难。岳飞在还未满一岁时就和母亲被卷入这场无情的水灾当中。吉人自有天相,岳飞和母亲被好人救下。当地的人们经历这场水灾之后家园尽毁,岳和这一家自从遭遇了这场无情的水灾,本无多少家产的岳家生活变得更加捉襟见肘。虽然家境拮据,但是岳飞的父亲为人善良忠厚,重义气,每当他看到邻里谁有困难,他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救济困难的人。父亲的美德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岳飞,这也影响着他塑造一个善良的人格。几年之后,岳飞多了一个弟弟,名叫岳翱,这样一来,家庭生活的负担就更大了。俗话说得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因此,岳飞还在幼年时,就需要下地劳动,砍柴,挖土,种庄稼等等。劳累的农活使他对农民的艰辛深有体会,也让他更加敬佩自己的父亲,让他的性格更加质朴醇厚。
岳飞的老师是位叫做周侗的老人。周侗文武双全,德才兼备,德高望重。他曾经是宋军的将领,因为看不惯朝廷的所作所为,和官府的腐败不堪,才隐居到岳家庄,在私塾教书。
然而,岳飞并不是直接去私塾上学,成为周侗的学生的。当时,岳飞家里贫困,没钱上学,私塾里有几个调皮捣蛋的学生,最出名的就是王贵这几个学生。他们曾经气走过无数个私塾里的老师,唯独遇到周侗,王贵这几个调皮学生逊色许多。王贵让岳飞打扮成他们的小厮,在墙外旁听,这样,外人就会以为这是大户人家服侍少爷的仆人,就不会赶走岳飞了。其中一次,周侗出了一个题目,让学生根据题目写一篇文章,这就难住王贵这些平时不好好学习的调皮学生了。他们几个让岳飞代写,岳飞在百般无奈下帮他们写了文章。周侗自是知道这几个学生肚子里有多少墨水,很清楚这文章不是他们自己写的,在周侗的盘问之下,他知道这几篇文章都是出自岳飞之手。这一个孩童只是在门外的旁听生,竟有如此笔墨,这让周侗大吃一惊。他立即出门去找寻岳飞,烈日炎炎之下,岳飞汗流浃背的用木棍在沙地上专心的练习文笔,一刹那间,周侗豁然开朗,觉得自己找到了衣钵的传人。于是,他免费收岳飞为徒。在周侗这位德才兼备的老师的教导下,岳飞的进步卓越。
开封陷落的消息传开后,北宋各地守将纷纷扯起勤王抗金的大旗。靖康元年十二月,康王赵构在相州正式开大元帅府,打出了抗金旗号。恰在此时,岳飞和妻儿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后,终于回到相州。在山河支离破碎之时,相州虽然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役,但其景象却与战场上一样凄惨。岳母姚氏说“为母虽未读过书,但圣贤之言还是略有耳闻。自古以来,忠孝两难全。忠孝,忠在前,孝在后。你虽不忍心让我独自在家过活,但是,你若能够为国家尽忠,也会光宗耀祖,我这脸上也会有光!你就别犹豫了,快去吧!”“儿子定然不会忘记母亲的教诲!”于是,岳母姚氏名岳飞将上衣脱下,用针在岳飞的背上,一针一针的刺下了“尽忠报国”这四个大字,以时时刻刻提醒岳飞不忘初心。随后岳飞告别母亲妻儿,投奔大元帅府的勤王之师去了。
在宋金对峙的历史时期,岳飞连结河朔的民间抗金武装,率领岳家军四次北伐,三元淮西,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为两宋以来最年轻的建节封侯者,被历史学家誉为宋、辽、金、西夏时期最为杰出的军事统帅和南宋中兴四将之首。甚至金军统帅完颜兀术都曾感叹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此时的完颜兀术被韩世忠逼的领兵且战且退,往建康退去。建康已经成为金军在江南仅有的立足点。岳飞见收复建康的时机已经成熟,立即领兵经常州向建康府方向挺进。岳飞抵达常州时,完颜兀术的殿后军队还在攻打常州。岳飞率部迎敌,四战四捷,打败金军,金军慌忙向西撤退,岳飞紧追不舍,又在镇江东再次大败金军。金军已经全部缩退到建康府,但兵力依然十分强大。岳飞在这时候也抵达建康府境内。岳飞清醒的意识到,金军虽然屡战屡败,但在兵力上依然占据优势,而且这种情况在一定时间内无法减退势力。一则,宋军的精锐部队在组织金军南侵的过程中损失太大,剩下的也大都位于安府附近,抵达建康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二则,宋军防线太长,无法尽数集结到建康。岳飞清楚的认识到,在这种情况吓,想要围歼金军几乎是不可能的。最现实的做法是自南而北,驱逐金军过江,趁势收复建康。终于在岳飞的领导之下,岳家军的奋勇杀敌,击退了金军。岳飞成功收复建康。
自古英雄遭天妒。岳飞被秦桧诬陷,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并被杀害。天大的冤案就这样成立了。岳飞虽然死了,但是他的英雄气概永留人间。他带领岳家军奋勇杀敌,为国家做出的奉献永远都在。百姓唾弃秦桧,并坐了雕像,让秦桧永远跪在英雄的庙前赎罪。最后以岳飞的《满江红》作为结尾: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参考书籍:《岳飞的故事》、《岳飞》)
身陷“性别”风波亭的《满江红》
《满江红》上映至今,虽然票房成绩喜人,但也受到了一些争议,在竞争对手与饭圈黑粉的轮番拉踩之下,目前最匪夷所思的指控,就是“辱女”。
而这顶大帽子的由来,即片中鹰犬逼问行刺者时,做出强暴女主角瑶琴的态势,眼见后者不肯就范,就加多参与人数。
据说上述情节令一些观众感到不适,继而有了微博的一条热搜,叫“性暴力的展示在电影中不是必需的”。这句话出自《女人们的谈话》的导演萨拉·波莉(Sarah Polley),原句是“每次我在电影中看到直白的性侵画面都会感到不适。性暴力的展示在电影中不是必需的。更需要展示的是受害者的创伤,以及她们如何前行”。
仅从字面意义上,我赞同波莉导演的发言,但我认为在评述一部中国电影时援引这番话,同样不是十分必要。因为国内外的审查标准大相径庭,我们的院线电影对于性的禁忌,远比采取分级制的欧美影坛严苛,后者那里难以接受的尺度,本就不太可能出现在国内的大银幕。
这原本是展开相关讨论前的常识,却异乎寻常地被“批评者”们忽略了。
我无法判断这些“感到不适”的观众是都去看了《满江红》,还是只是在微博话题页下道听途说,至少我没有看到电影有明目张胆的辱女意向。相反,《满江红》塑造了明辨是非、勇敢无畏、舍生取义的女性形象,非但没有看轻女性,甚至在推动情节的决断时刻,对女性角色委以重任。
可以这样讲,被扣上辱女帽子的《满江红》,遭遇的是风波亭式的冤枉。
意大利名导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就讲过这样一句话:“电影并非是在创造暴力,它只是证明暴力的存在。”
当我们在讨论电影“辱女”与否之前,一个基本前提应当是:一部电影表现了暴力,并不等同于创作者认同并且宣扬暴力。
因此,对影视作品动机的判定,表面上关于暴力,实际上关于观看,表面上看是一个内容程度的问题,实际却涉及了观众如何区分现实与银幕。
阿根廷导演加斯帕·诺(Gaspar Noé)2002年的作品《不可撤销》或许是在电影中展示性暴力的典型范例。片中以纪实手段拍摄了一场长达9分钟的强暴戏,由莫妮卡·贝鲁奇饰演女主在遭遇性侵后,面部还被变态的街头混混打得鲜血淋漓。这样的暴力镜头给电影带来了消极的舆论评价,当年的首映式上便有观众自发离席。
同样引发离席和声讨的还有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2018年的作品《此房是我造》,这部电影除了大玩宗教梗,还出现了很多杀人情节,其中一幕是男主在高处用一把猎枪先后猎杀了妻子和女儿,整个步骤有条不紊,就像在林间打兔子。
关于导演们拍摄这类暴力镜头是否有损职业道德,是介于艺术与伦理的复杂议题,并不存在定论,通常情况下观众与作者达成的默契是:如果自觉过于感性,或是对施虐狂式的镜头感到不适,那就尽量避免去看这类电影。
事实上,观看与传播并不会在现实中助推暴力,对暴力行径的避讳与掩藏,反而屡屡导致暴力在现实世界的肆意疯长。就好比对战争片而言,如果不真实地刻画战场的血腥与残酷,不最大限度地呈现暴力机器对血肉之躯的摧残,就难以调动观众的反感本能,令“厌战”不至于遁入标语与主义的虚无。
至于是否允许暴力被重新演绎,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就认为:“没有直接书写创伤本身这种事,这是因为创伤——尽管有时候创伤和某些特定事件有关,却无法被限于在那段特定时间内。创伤意味着经验的破坏和断裂,而其影响和效应还会在日后重现。”
换句话说,二次伤害不来源于暴力被提及,而是来源于暴力本身。而当人们在某种观念下越是刻意回避和否认暴力,暴力的内在创伤就越是存在被放大的风险。
但无论我们如何界定暴力的作用和限度,都不应该从创作者的手段假定他的立场,将艺术的武器用于对艺术的批判。否则,无论你支持的是哪一种艺术,艺术都将不复存在。
在《满江红》里,士兵推搡并撕扯女主瑶琴的片段是否构成性暴力,并不存在严重分歧,值得思考的关键,是这一行为更偏向于性侵,还是暴力。
如果只有暴力,没有性侵,就谈不上性暴力,除非把性暴力作扩大化解释,即对一切性别采取的暴力都算性暴力,但这种解释必将指向虚无。就像电影表现的那样,当暴力变得无差别,刀俎并不会去区分鱼肉是雌是雄。
在电影开场,易烊千玺饰演的孙均在审问效用兵时,没问两句话就一刀一个,贯穿全片的草菅人命从这一刻已然启程,远早于舞女被何立从背后刺穿。如果着重关注性别,那么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开刀是从男性开始的,片中被格杀的男性角色也远远多于女性角色。
无论效用兵、打更兵、马夫还是舞女,在片中都遭遇了极致的暴力——这是小人物集体遭遇的普遍性;真正的区别所在,是瑶琴的状况多了一丝侮辱成分——这是女性角色面临的特殊性。
那么问题来了,剧情是否一定要给女性角色安排这个特殊性?是否一定要呈现“瑶琴被扒衣服,被一众士兵慢慢吞没”的严酷画面。
在我看来答案是肯定的,但绝非建立在一部分女性观众臆想中的“香艳戏码不可或缺,是吸引男性观众的不二法门”的基础上。
舞女瑶琴是张大的软肋,观众对瑶琴即将面临的处境感到难以忍受,其实正是电影中张大的心理——所有人都不忍看到女主被强暴,宁可她直接被杀或是换一种酷刑,这恰恰说明暴力机关选对了刑罚,刑罚在这一刻的目的,不是竭尽所能折磨受刑者,而是逼迫受刑者的同志就范。
既然性暴力比直接索命还令人难受,那么何立等人当然要把刀戳在张大的软肋上。不仅其它肉刑很难达到这个效果,一旦用刑过重导致瑶琴直接死亡,对审判者来说,反倒失去了唯一可以要挟张大的筹码。
至于被炮制的“贞操观”,则纯属网友对电影的欲加之罪。
张大说“杀了她,别糟蹋了她”,并非一些人臆想中的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对心系瑶琴的张大来说,如果瑶琴必有一死,那么最痛快的死法当然是“速死”,而不是在死前还要再受**,比起一刀抹脖子,后者当然是双重伤害。
这里不妨多说一句。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虽多被用于约束女性,但也并非一定与性相关,还可以强调原则与立场。
比如一个人快饿死了,草根树皮昆虫耗子都吃完了,不得已跑到其它地界要饭,或是吃了敌方空投的救济粮,按照“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精神,这就是典型的因小失大,给己方丢了大人、抹了大黑,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比当地的面子还重。
片中的张大、瑶琴一行,为了心中的正义不惜对抗强权,自然是处于上述迂腐价值观的反面。
无论杀死瑶琴还是折磨瑶琴,都令人感到不适,不仅会令女性观众感到不适,也会令男性观众感到不适,这里不会有本质区别,并非像一些人认为的,当男性观众看到瑶琴被施暴,就会在心底欢呼雀跃。
我真正想说的是,令人感到不适,是否一定是电影的问题,或者说,这是否是个问题?
一部电影足够深刻,足够扣人心弦,足够戳破幻象,足够切入命脉,它就一定会让人感到不适。但这个不适本身是可贵的,它让你产生刺痛感和焦灼感,这说明它的叙事真正落地生根,而不是过后即抛的温吞水。
令人感到“舒适”并非是一切电影的目的,它也不应当是一切电影的目的,希望在银幕上寻找舒适的人,或许是看惯了“爆米花”,也只能去看“爆米花”。要求一切电影都变成“爆米花”或“样板戏”,确实能令一部分人感到舒适,同时也会令大部分人感到无聊。
在我看来,一个成熟的社会不应该警惕种种因素可能导致的“不适”,而是应该警惕一部分人由于无法正确处理与“不适”的关系,而频频迁怒他人。
今天一部分女性观众感到某种不适构成了“辱女”,明天就可能有一部分男性观众感到某些不爽构成了“辱男”。这种“唯我独尊”的念头还可从性别扩散到一切事物,并且不断升级,最终造成的局面是:看似你只切掉了那1/10“有毒有害”的部分,但剩下的9/10均有可能是他人的1/10,都有概率会被另一些人认为“有毒有害”。
学渣看到拍学霸,有可能感到不适;
穷人看到拍富人,有可能感到不适;
单身看到拍情侣,也有可能感到不适;
这个公式还可以往下列一千个、一万个。是不是令前者感到不适的内容,较好统统取缔掉呢?
举一个大家都明白的例子,当代有很多展现屠杀的影视作品,无论是中国导演拍还是外国导演拍,相关场面肯定也会令人感到不适,是否也都自动屏蔽掉呢,或是把杀戮的方式换成令所有人感到“温和、妥当、可接受”?是否为了避免麻烦和争议,较好以后都不要拍了,不仅不要拍,干脆不要提,甚至直接否认这件事的存在呢?
果真是这样一种态度,日本右翼很难不点赞。
话说回来,《满江红》中舞女们的悲剧或许来自创作者对某种历史宿命的提纯。这种宿命可以概括为:生逢战局,无论战争性质如何,承受苦难的都是最底层的普通人。而在这些普通人里,老弱妇孺的命运又最为悲惨。
宋人庄绰在《鸡肋编》中记述道,靖康之难后,广大的中原地带遭遇了严重破坏,到处是荒地与饿殍。无论盗贼还是官兵,在乱世中纷纷吃起人肉。绍兴三年(1133年),山东登州的义军领袖范温南下钱塘,携带的军粮便是人肉干。连抗金义士都在吃人,可见民间“易子而食”的普遍。
书中还记载了当时的“食谱”,老瘦男子被称为“饶把火”,年轻妇人被称为“不羡羊”,小儿被称为“和骨烂”,以上统称为“两脚羊”。要论不忍与不适,恐怕没有什么电影能与真实发生的历史相较,但电影所表现的与上述惨剧倒是有一点相似,即弱势群体在凶年尤其难逃被支配、被摆布、被收割的厄运。
正因如此,非说《满江红》辱没了某一种性别,在我看来是不准确的,因为严谨地看,权力意识中根本不会存在性别意识的位置——瑶琴和张大一样,只是蝼蚁,是物件,是劈柴,不会被权贵当作人来看待。而当一个人的性命都被看作无足轻重,她是什么性别自然更加无关紧要。
这甚至不是历史环境的问题——好像只有宋代人是如此,而作为21世纪的创作者,就必须用现代的性别观去塑造历史故事——电影本质上描述的是一种权力语境,这种语境在不同年代会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绝非只存在于古代,或是用于描绘古代的银幕之上。现实情境中瑶琴们的待遇,恐怕比电影中呈现的更悲催,只不过我们看不到罢了。
《满江红》虽然充斥喜剧元素,但我却没有把它看作一个四合院里的剧本杀,相反,它给我的感觉是极度肃杀、压抑与悲愤。院内里里外外的禁军与内侍系统,严丝合缝地演绎了暴力机器上足发条的状态,他们枕戈待旦,惟命一人,准备碾碎一切草芥。
以上就是风波亭里满江红是什么生肖?的详细内容,希望通过阅读小编的文章之后能够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