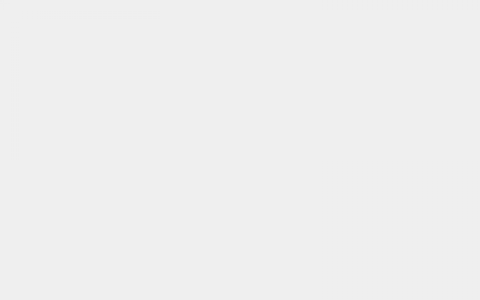1 个回答

(图文无关)南方的天气还很闷热,只有到了入夜时分,才会有一阵湿润的凉风从珠江吹过来。 (南方周末记者 冯飞/图)
这个可怕的想法时不时会跳出来困扰我——是我害死了母亲。是我导致了她的死亡。
在母亲进城见弗朗西斯医生的那几天,我每天都在广州中山五路上的一家咖啡馆写小说。那是临近仲秋的一段时光,南方的天气还很闷热,只有到了入夜时分,才会有一阵湿润的凉风从珠江吹过来。
那时的我刚辞职三个月,决意要在家里写小说,不再出外工作。我既忐忑又怀抱着希望。因为是陪夏木南下出差,减轻了许多家务的负担,所以我能更专注地写作。我开始写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回乡参加丧礼和房子的故事。
最初的那几日,我的状态还不错,故事的进展很顺利。可是,就在我着手写故事里的那个母亲时,整个世界仿佛停滞不前了。无疑我是在将自己的生活投射到我正在写的故事之中。当我试图描绘小说中的那个母亲时,我脑海里浮现的却是自己的母亲的形象。母亲的容貌和声音越来越清晰。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厌烦的感觉。
那是一次独特的经历。我从未受困于这样的感觉之中。厌恶、烦闷的情绪不断袭来。无法将母亲的身影从我脑海中驱逐出去使我苦恼不已。我深刻意识到原来自己无法完全摆脱母亲,即使我已离开乌拉港那么久,那么远。
母亲的性格中有一些我讨厌的特质。长久以来,我甚至不惮于公开嘲讽、批评她。其实她是一个真实的人,不擅长伪装,在对富人笑脸相迎(父亲总说那是谄媚)的同时,也会对穷苦人伸出援手,表现出真诚的同情和大度。不过她的善举背后似乎总隐藏着一丝炫耀和迷信的意味。她极度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的说法。因此她的那些也许是出于善意的行为有时候很容易遭到怀疑和鄙夷。
母亲对金钱和数字的在意是我曾经厌恶的。她几乎每一句脱口而出的话都会提到金钱。
“这是我那天在商场买的,九十九块,有打折。”
“这红毛丹很好吃,一斤六块半。”
“她去阿英的婚礼才给五十块红包!”
她有专门用来记账的记事簿。不止一本。我憎恶那些散发着廉价仿真皮革和油墨的气味的记事本。那些本子就躺在抽屉里,抽屉没有上锁,以便随时可以打开,像取出狩猎步枪那样将记事本取出来,迅速又决绝。
她使用那些记事本的方式确实像是在使用猎枪。我们这些孩子是她的猎物。每当她与某个孩子发生一场与金钱有关的争执时,她会大踏步地走到房间,取出记事本,认真又快速地翻找着,然后把找到的账目拿给对方看。
“看,这里写得很清楚,明明是四百块。”在把记事本递给孩子时,她会加上这么一句。
那个时候,这样一句话总是带有残酷的杀伤力。那是对我们下的判决,记事本上的数字则是我们这些孩子的罪证。
看,上面都有我们的手迹了。
06.01.2002 学杂费 RM2512
06.01.2002 生活费 RM400
21.02.2002 生活费 RM400
01.04.2002 生活费 RM200
05.05.2002 生活费 RM200
01.06.2002 生活费 RM200
01.07.2002 生活费 RM200
01.08.2002 生活费 RM300
15.08.2002 杂费 RM220
01.09.2002 生活费 RM200
01.10.2002 生活费 RM200
01.11.2002 生活费 RM200
06.12.2002 生活费 RM300
二零零二年。那是我在学院念中文系的第一年。即便有了贷学金,我还是需要母亲的资助。那些年,我们几个孩子相继到城里或国外上学,靠奖学金或贷学金,有时候也打零工挣生活费。但钱总是不够。我们仍然需要母亲的资助(此时此刻,写下这句话仍然使我感到羞耻不已)。
在领钱时,我们需要在记事本上写下日期、金额及钱的用途。每个人负责记自己的账目。如果不在家,母亲或二姐便会代劳。偶尔我们还得在账目下面签自己的名字。
这种感觉很不好受。仿佛你一生下来就注定背负着债务,永远还不清的债务。我们多年来就是活在这样的阴影之下的。至少我是这样的。
于是,在这样的家庭,挣多少钱便意味着一个人有多成功和坚韧。因为这能证明你有能力偿还债务,有能力报恩,能自食其力。
讽刺的是,我竟然在不知不觉中继承了母亲这惹人嫌恶的性格。我在二十八岁那年才发现这个事实。某个冬夜,我和室友惠惠坐在客厅里闲聊,从日常生活聊到了原生家庭。
“你知道吗?这是你从你的家族继承来的。你看所有东西都有价签,每一样东西在你眼里都是明码标价的。”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这么说。也许她是对的。
“因为钱对你们来说非常重要。所有东西都需要花钱才能得到,所以你们这么在乎钱。”惠惠继续说道。
我还想起曾经有人提醒我千万别问一个人的薪资有多少。这是隐私,人们说。这也是我上大学以后才懂得的事。
你终究是你母亲的孩子,不管你愿不愿意。你看你多像她。
孩子们毕业后,她开始在记事本上记孩子给她多少家用。她还习惯将哪件新衣是哪个孩子(几乎都是大姐)送的这样的事挂在嘴上。我是极少被提及的那个孩子。我给的家用和送的东西实在微不足道。
我仿佛总是急切想摆脱这一切。我害怕和她一样。我不要像她那样对数字极为敏感和拥有惊人的记忆力。我不要像她那样在记事本上记账。我不会动不动就提餐桌上的饭菜值多少钱。我不会露出一副自以为无私奉献的嘴脸。
然而这只是徒劳无功的逃离。多年以后,当我结了婚,开始与另一个家庭有了哪怕是最淡漠、疏远的联系,发现自己不过是从一摊泥淖陷落到又一摊泥淖里(那你指望生活是什么?)时,我对眼下的生活不禁感到失望、愤怒,不知不觉便自怨自艾,充满了怨毒。
这一切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生病后,母亲开始提到我们这些孩子在幼年时花了她多少钱。当时她、妹妹和我在卧室里,她在整理珍藏多年的首饰,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在对话越来越激烈时,为了证明她的记忆无误,母亲再次拿出她的记事本来。
“你自己看,看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这一次,她的语气和缓许多,甚至显得有气无力。
母亲很快就回到隔壁的卧室睡下了。她走后,我和妹妹不停地翻看她的记事本,直到我们俩都精疲力竭为止。
我们究竟在找什么呢?我想我们都在寻求一种自我肯定。我们想找出足以证明自己的能耐的证据。毕竟我们的生活已经够艰难了。
然而所有努力都是白费力气。你无法抹去事实。你也无法在你还牙牙学语时就完全独立。这怎么可能呢?
“如果是这样,那倒不如不要生孩子。”大姐说。
直到最后她还在不停地记账。没完没了。她记下谁给她钱,还有给了多少。一千。五百。三百。在一本行事历上,她则记下自己欠了车衣女工多少钱。那是一本一九九五年的行事历,黑色,镶着金边,里面印着公历和回历日期。我认得它。那是从前父亲在印刷厂当运货司机时带回来的行事历。那时候父亲常常将厂里丢弃的行事历和书本带回家。我在那些行事历上写日记和抄写生词,母亲则写下了无数个对她来说意义深重的数字。
是啊,那些数字对她来说是那么的重要。她的丈夫后来不工作了,她当然必须承担起养家的责任了。不然她还能依靠谁?
是我的嫌恶导致了她的死亡吗?当时我差一点就要诅咒她了。当她进城见弗朗西斯医生时,我坐在咖啡馆里神情漠然、专注地写小说,以为自己的命运终将有所改变,于是更加决绝、冷酷,将她的身影从我的脑海里驱赶出去。是不是就在那一刻,那关键的一刻,深藏在她胆囊里的癌细胞就此暴发,疯狂生长?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父亲总这样嘲讽她。
“如果我不这样拼命工作,我们吃什么?吃什么?”后来她这样对我说。她不敢在父亲面前说这样的话。
凭什么她就不能记账,记下那些自己辛苦挣来的钱究竟花到哪里去了?
林雪虹